普法:于安思危 于治忧乱
本篇文章1705字,读完约4分钟
朱康有
“‘安思危,治忧。 』我们党诞生于内忧外患中,在苦难的挫折中成长,战胜风险挑战而成长,始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这是习大总书记年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进行的演说,深刻表明政治风险防范是党政治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面。

“安思危、治忧乱”,前半部分是《逸周书程典》《安思危、始思终》、《战国策楚策四》《臣闻之《春秋》,安思危、危险考虑到了安。 我不知道没有疾病的痛苦,没有疾病的祝福。 所以君子平息安思危、忧虑”,强调在平安的环境中必须考虑危难和风险,考虑稳定时可能发生的动乱。 必须防患于未然,充分估计困难和坏事,随时做好应对意外风险的思想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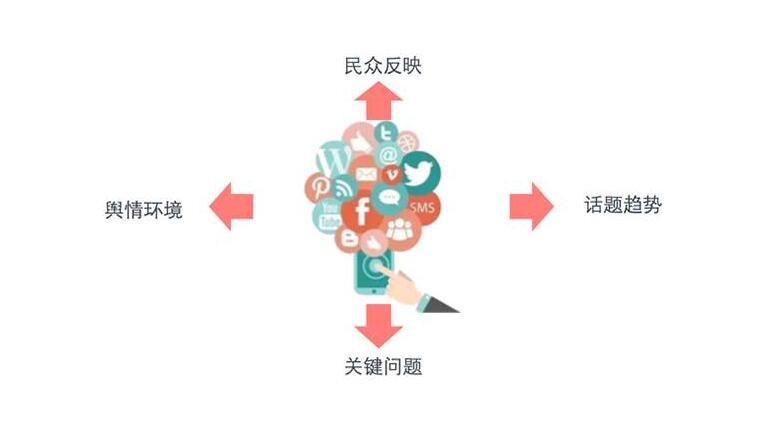
为什么从古至今政治家和思想家反复强调这一点? 其实,反映了对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性的认识。 社会的安与危,治与乱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从空间分布状况来看,安中有危险,治中多有紊乱。 从时间快速发展的过程来说,安可转危险,可治转混乱。 反之亦然。 但是人的视野往往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看不到一叶障目、泰山。 看一时,很难从长远来看。 《道德经》通过“反者道之动”的哲理警告说,矛盾双方“有无相生、难易相、长短相、优劣相倾、语音相和、前后相伴”的相互依存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两者。 《孙子兵法》还指出“乱生于治,胆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乱”由“治”产生,“胆怯”由“勇”产生,“弱”由“弱”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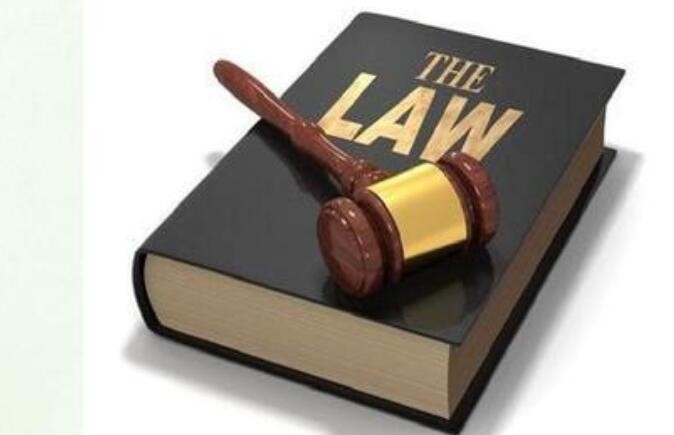
孔子著《春秋》关于十二世的事,是“杀你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细恶不断”,但由于“死者、自杀也是非人死的”,“昭然可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定于未然”中国的历史 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希望长治久安却无法摆脱“周期律”,陷入“后人悲伤不吸取教训,后人悲伤推翻后世”的宿命,在内忧外患中失去政权? 一个统治集团在草莽成立之初,流血牺牲,不惜万死,“苦难,玉汝于成”,但“打得天下”并不是说“能坐江山”。 许多盛极一时的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鉴于积极的毁灭教训,观察激励精图治,重视反贪婪腐败,赢得民心,巩固江山,但在中期,特别是后期,往往会奢侈到产生腐败之风生病。 因此,“外患”往往是外部原因,“内忧”容易被忽视,但却是导致失败的真正决策性因素。

转换的“契机”在哪里? 在苦难“如山”的时候,反而激发了彻底的大胆,旋转一个身体、一个政党的峰回路,使之复活,度过了极其困难的岁月,向上,向前迅速发展,真的很宝贵。 困难的是,一些忧患的发生正是最困难最困难的时期。 汉武帝变得雄壮后,从盛到衰,从“开元盛世”的唐明皇、清干隆后期开始走下坡路。 苏联共产党在20万党员时打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政权。 200万党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保卫了政权。 2000万党员自己打败了自己,失去了政权。 这些中外史上比比皆是的例子证明了什么? 大家认为“坚强、稳定、安全”的时候,赞美之声四起,在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期间,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忧患的意识吗? 明代的《钱公良测语》一书中说:“天下之祸不反生,顺生”,《淮南子说山训》说:“良医,治好无病,无病。 圣人总是治疗没有患者的患者,所以也没有患者”。 习大总书记警告全党,越是取得成绩越需要踩薄冰般的谨慎,越是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就越不要犯战术上、卓越的错误。 《易传》如何处理因处于强势位置而引起的加速转换问题? 其一,通过提供“君子安全、不忘危险、保存不忘死亡、治疗不忘混乱”的制约性思考方法,不让其单方面行为。 其二,不断修正自己,创新,尽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日新之事称为盛德”,日益更新,被称为盛德美行。

“忽也”和“忽”字清楚了一切。 这里的“忽”意味着突然,强调客观情况。 而且暗含结果的意外与人的主观失察密切相关。 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悲剧,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之一是“自己处理不了自己的问题”,陷入了“革命别人容易,革命自己难”的状况。 参考历史,我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政党,在政权业绩的光环下,容易发生无视自己不足的现象。 任务越重,风险考验就越大,要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 这才是决定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

(作者是北京市习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标题:普法:于安思危 于治忧乱 地址:http://www.leixj.com/pf/2021/0106/233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