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仲裁地在仲裁程序中的重要性
本篇文章2569字,读完约6分钟
宋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
仲裁地( seat of arbitration )在仲裁案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选定仲裁人一样重要,有学者认为选出什么样的仲裁人就有什么样的仲裁。 仲裁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仲裁的过程和结果,直接关系到仲裁当事人的根本好处,仲裁机构的公共说服力。 仲裁地的明确也是如此,仲裁地明确后,与仲裁案件相关的仲裁可能性、导论法及实体法、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仲裁裁决的取消、不承认或执行等问题与《仲裁地法》相关( lex arbitrii )。 换句话说,仲裁地的选定不仅会影响在该地进行的仲裁程序,还可能影响到之后的仲裁判断。

仲裁地明确后,会产生可能影响争议部分事项仲裁可能性的法律效果。 争端的一些事项是否允许仲裁需要根据仲裁地法进行评价。 因为对争端的一些事项的仲裁可能性问题各国的立法规定不同,只有仲裁地国法律允许的纠纷的一些事项可以约定在仲裁地国仲裁。 否则,违反仲裁可能性,仲裁裁决有被取消的风险。 二是可能影响仲裁协议的存在,比较有效。 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比较有效的争论最终由仲裁地法院解释和认定。 三是可能影响仲裁裁决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庭选定仲裁地的,仲裁裁决书应当记载仲裁地是仲裁裁决书的制作地,以便评价仲裁裁决的国籍。 当事人判断仲裁裁决有被取消的理由时,只能要求仲裁地法院取消仲裁裁决。

仲裁判断后,仲裁判断结果的实现通常需要仲裁地法院的支持和合作。 因此仲裁地的正确选择是实现仲裁目的的重要条件。 一般来说,仲裁地的选择需要考虑: (1)仲裁地国重视国际仲裁的迅速发展,同时有支持仲裁的良好制度设计。 用仲裁方法处理国际间的经贸争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仲裁机构来应对越来越多的纷争处理。 例如,在英国伦敦设立的“商事法院”( commercial court )专门解决商事纠纷。 此外,英国“技术和工程法院”(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court )来自具有工商专业背景、法律实践经验丰富的律师,专门解决工程和技术类案件。 一般来说,这些国家是纽约条约的成员国,也是保障仲裁条约的条约缔约国,这样的国家往往是选择仲裁地时优先考虑的国家。 (二)仲裁地具有先进的仲裁立法,而且仲裁地法院对仲裁持支持态度。 仲裁判断结果的最终实现往往需要利用一国法院的司法强制力。 法国、瑞士等国的仲裁立法很先进,对司法仲裁的支持力也很大。 但是,有些国家的法院对仲裁持谨慎态度,始终警惕仲裁侵犯了国家司法主权。 例如,严格解释仲裁条款的存在及比较有效性,将有瑕疵的仲裁条款解释为无效条款。 例如,不同意以前传达的仲裁法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临时仲裁,对仲裁出现了“不友好”的理念。 这些是当事人、仲裁庭和仲裁机构选择仲裁地时应观察的国家或地区。 (3)适当的仲裁地有利于节约费用提高效率。 通常,当事人对仲裁有合理的期待,仲裁协议的效力容易被肯定,除了仲裁裁决迅速执行外,当事人为完成仲裁程序承担的费用也在其期待范围内。 仲裁地除了对仲裁员、当事人方便以外,还需要具备开庭审理所需的场所和必要设备,以及适当的仲裁秘书和翻译人员等,节约当事人不必要的支出。

仲裁地影响仲裁裁决的国籍,国籍显示了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之源。 因为仲裁如果不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国内法相关,就不会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根据国际仲裁条约、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以及各国商事仲裁立法中关于仲裁地的规定解体,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地通常审查仲裁协议中有无仲裁地的约定,如果存在,则按照以此为仲裁裁决地的评价顺序。 这是仲裁协议的本质特征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结果。 其次,仲裁协议没有约定仲裁地的,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明确仲裁裁决地。 仲裁地标准成为明确目前国际公认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主要标准,因此仲裁地的明确化对评价仲裁裁决国籍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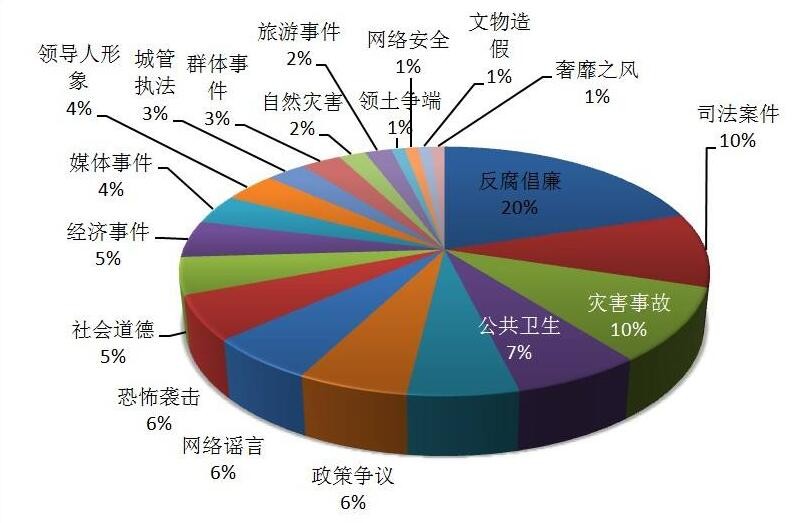
根据我国现行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必须承诺将争端提交给某个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否则仲裁协议视为无效。 我国仲裁立法强调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效力的重要性,无视仲裁地的重要功能,脱离了国际仲裁理论和实践,但现实的仲裁实践呼吁重视仲裁地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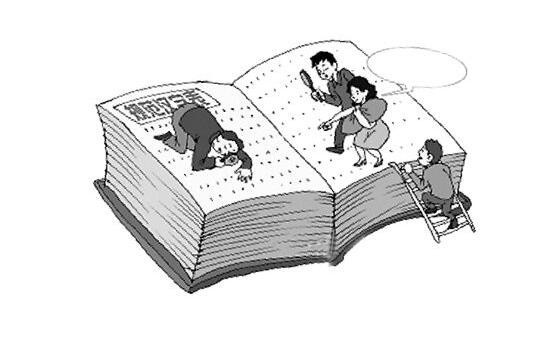
(一)仲裁地法作为确认仲裁协议适用法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的法律。 未约定适用的法律也不清楚仲裁地或仲裁地约定的,适用法院的法律。 ”这也是司法解释中首次出现“仲裁地”的概念。 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8条的规定是:“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或者仲裁地的法律。 》该条的规定是关于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当事人签订的仲裁协议没有规定约定仲裁机构和仲裁地,但可以根据该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认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地。 《最高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结合司法实践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适用的仲裁规则明确仲裁机构或仲裁地的,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所称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地 实践中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和仲裁地的法律可能会产生不同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情况,从支持仲裁的大致观点出发,必须适用确认仲裁协议比较有效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二)将仲裁地无限作为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表的《关于香港仲裁判断在内地执行问题的通知》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的临时仲裁判断、icc仲裁判断在内地被批准和执行的不是《纽约条约》,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作为我国仲裁理念转变的证据,也可以同意用《仲裁地基准》识别区域间仲裁判断的属性。 即在香港进行的临时仲裁判断、icc仲裁判断是香港仲裁判断,在内地的承认和执行应该适用“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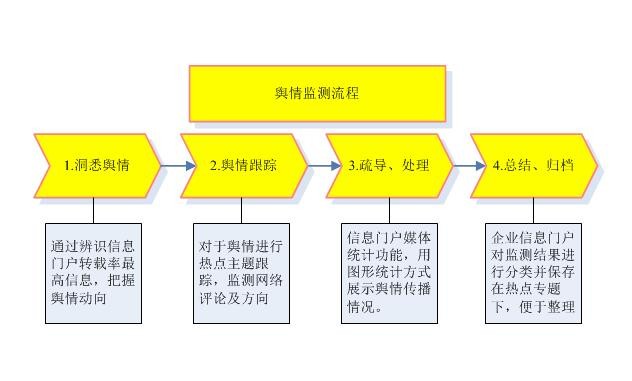
由于仲裁法的修改滞后,仲裁地在我国仲裁实践中缺乏重要功能,与仲裁制度的国际化有差异。 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仲裁重要性的今天,如果没有仲裁地制度的国际化,让中国成为“仲裁优先地”也将成为空谈。
标题:普法:仲裁地在仲裁程序中的重要性 地址:http://www.leixj.com/pf/2020/1225/192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