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安乐死”的两个说法
本篇文章1194字,读完约3分钟
□刘星
苏北有益林町,被称为“小上海”。 镇上有个叫陈的女人。 1993年,陈某女老师捏着胸患了癌症。 病魔痛苦,痛苦严重,丈夫日夜呻吟得厉害。 第二年,女性终于看不到这种惨状,在丈夫的要求下结束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

不到两天,局子里来了人,带着女人,然后把她推上了公会堂。 公审法官翻阅刑法草案,认为是故意杀人,因此故意杀人罪成立,下达了刑期3年的判决书。 女人就这样被送进了大狱。 法官说,不能非法夺去别人的生命。 即使受害者自己高兴,取命的行为依然是对别人生命权的公然侵犯。 这是社会危害性的意思。 用专业术语来说,女性主观上是有意的,客观上有行为,罪是逃脱不了的。 当然,法官还说,由于情节轻微,判决了三年。

没有独特的东西。
前几天,北方的一个城市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有个青年,有孝敬父母的心,母亲得了不治之症接近死亡,所以不能忍受母亲的痛苦,要求医生吃药促使死亡。 后来又从局子里来了,二话不说,逮捕了年轻人和医生回国,同样推上了公所。 但是,法官的判决很有趣。 法官说故意杀人是无可争议的。 社会危害性的定论也不能商量。 只是读了判决书,故意杀人罪不成立。 理由很简单:情节轻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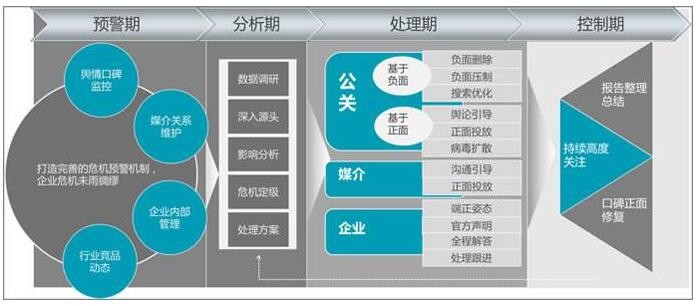
熟悉刑名的人知道情节轻微是犯罪圈内的事件。 情节轻微是犯罪圈外的事。 可见“轻微”、“显著轻微”等词语富于灵活性。 刑法的规定相当“灵活”。

对于前一件事和后一件事,人们喜欢说那是“安乐死”。
“安乐死”是近年来流行不断的法律话题,要求合法化的呼声高涨。 很多人判断这个死比较好。 一个可以减少患者的痛苦,二个可以解除亲属的负担,三个可以阻止医疗的浪费,四个可以创造人们生命观念的新风俗。 当然,也有相反的话。 反对者说人的生命太宝贵了,失去了无法挽回,只有这样才能要求人们不惜保护它。

“安乐死”不现实,太多太杂了。 可能是因为不清楚,不知道,我们的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总是喜欢沉默,沉默就像黄金一样。 受此影响,有人抱怨法律无视“安乐死”的问题有违时代潮流的新的迅速发展。

但是,以下认为现在的法律状态也很好。 不一定不能处理现实问题。 争论还不一致时,法官在法律框架内,巧妙地使用法律的一些“灵活”规定,是处理变化剧烈的事件的方法,不是调节“安乐死”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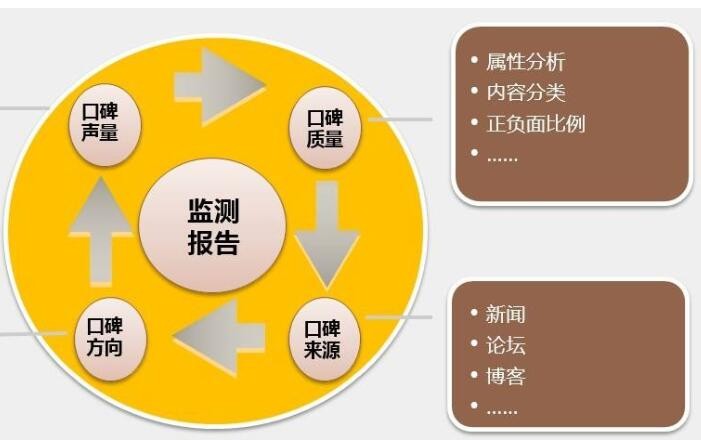
看,在第一个案件中,法官的判决可以提醒人们以“享受安宁”的方式“解放”。 通常,你必须背负犯罪的名声,在大狱服刑几年。 那样的话,企图者会慎重且慎重地仔细考虑是否应该插手。 在后者的案件中,法官的判决也可以包括人们的观察:如果情况特殊,患者真的没救了,痛苦非常不说,而且如果接近死亡,道义和法律很可能静静地站在“安乐死”一边。 用隐藏的方法,有条件就付出代价默许。 这样,人们就会更肯定、更勇敢地完成生命的升华。

当然,社会意见基本一致,但同时立法机关和最高法院保持沉默的话,两种说法的灵活性应该成为一种说法的“稳定性”。
标题:普法:“安乐死”的两个说法 地址:http://www.leixj.com/pf/2020/1224/18752.html
上一篇:普法:徜徉于经验与理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