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交通肇事救助后又消极逃避处罚的定性
本篇文章1231字,读完约3分钟
黄健刘兴元
吕某被告驾驶重型半挂车行驶到某个十字路口时,与王某驾驶的轿车相撞,引起了王某受重伤,小汽车乘员周某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 根据警察部门的认定,吕某将承担这次事故的首要责任。 事件发生后,吕某亲自送王某、周某去医院后,无故离开。 后吕某向警察部门询问。 一个月后,本案定性为刑事案件,吕某被公安机关通知不能拒绝,随后在家中被捕归案。 吕某因涉嫌交通事故被人民法院公诉后,吕某救助伤者后,比较了从刑事处罚中消极逃避的行为是否属于“交通事故逃亡”的加重处罚情节,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吕某这样的情况没有通报就把伤员送到医院后,拒绝提交给事件合作事务机关,构成了交通事故的逃脱方案。 第二种观点认为,吕某积极救助伤者,并亲自接受过事务所的咨询,不构成交通事故的逃脱。

我认为评价“交通事故逃脱”状况的首要依据是是否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 对“交通事故逃脱”设置加重处罚的方案,有“逃避法律追究说”和“逃避救助说”两个论断依据。 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在交通事故中发生受害者受伤的危机状况的情况下,交通加害者有积极救助的义务。 这时,这个肇事者是拯救受害者的第一负责人。 刑罚中对“逃跑”情况加重处罚的社会价值是,交通肇事者不履行救助义务会增加伤者的伤亡风险,从而加剧或扩大现有受害者身上的侵害程度,在量刑方面有必要加以区别。 据说“逃离交通事故”的核心本质是“逃避救助”。 在本案中,吕某把受害者送到医院进行急救治疗,降低了人身损害扩大的风险,实际上履行了救助义务。 未经通报而派遣医生后的行为不应该抵消这种积极救助的表现。

积极实施救助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价值发生冲突的,必须合理取舍。 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的价值观有矛盾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优先采取第一价值观,即人的人身权益乃至生命,始终处于第一位。 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出租车司机选择载着急症患者去看医生,闯红灯,但相关部门一致认为不对违反进行行政处罚的价值观。 另外,对于故意杀人和强盗等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处罚没有将犯罪后的“逃跑”作为量刑恶化。 反观的话,如果怀疑是交通事故的行为者选择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其他时间、地点隐蔽逃跑,由于在事故现场不存在必须用刑法保护的受害者的法益,因此也没有必要认定这种后续行为是“逃跑”。 本案被告人吕某的行为表现是这样的。 司法实践中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单纯把“逃避法律追究”作为“逃避”的认定基准,加害者留在现场亲自接受警察的解决成为法定义务,加害者和嫌疑人在现场如实供述事件的过程,自首是一定的困难。 对于更严重的刑事暴力犯罪,这种行为可以视为自首表现。 即适应处罚罪的责任大体上必须得到公平合理的贯彻实施。

综上所述,关于交通事故是否是逃跑状况,必须综合很多情况和法理来判定。 对吕某被告行为的量刑处罚,然后逃避案件机关的案件,拒绝刑事解决的行为的表现,可以作为量刑的考虑因素,不得与“逃跑”的加重情节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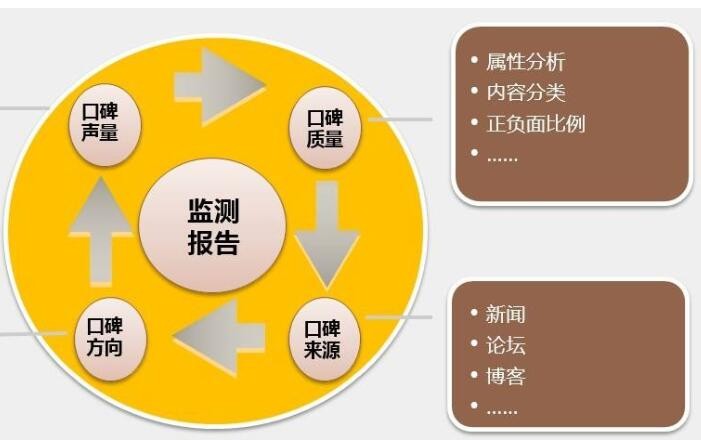
(作者单位:河南省桐柏县人民法院)
标题:普法:交通肇事救助后又消极逃避处罚的定性 地址:http://www.leixj.com/pf/2020/1222/1808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