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龙筋凤髓判》中的法和人情
本篇文章3464字,读完约9分钟
□李驰
在我国古代法中案例一直流传至今,张所著案例集《龙筋凤髓判》是典型的代表。 张是唐代有名的律学家、文学家,才华横溢,著述众多。 史书张彟说:“下笔的速度,著述特别多,语言很滑稽。 时间天下闻名,既聪明又不肖,都背着那句话。 ”名声从当时开始就扩展到海外,其影响之大是可以充分看到的。 “新罗、日本东夷诸藩特别重视那句话,每次使用者早上都要拿出金贝购买那句话,其才能远播。 》《龙筋凤髓判》是张彟最重要的法学著作,也是唐代预定判决的代表。 判决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资料,没有法律效力,事件中的人物也经常隐瞒真名。 但是,霍存福考证显示,《龙筋凤髓判》的很多例子都来自历史的真实事实,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龙筋凤髓判》判目解读))因此,对唐代司法活动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后者也批评“龙筋凤髓判”,张謇的判决书不能说“不背人情,符合法意”,“百判纯是当时的文格,全类俳句,但知道堆叠故事,但用遮光罪法无法深入,很难阅读。 (《容斋随笔续集》)中,“龙筋凤髓判”真的不能“不背人情,符合法意”吗? 实际上,张彟的判决书文风华丽,但审判讲理基本上符合法律,兼顾了人情。

一、法律是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
律与礼是唐代第一法律的根源,也是《龙筋凤髓判》中定罪量刑、审判辩护的第一依据。 根据现代法学理论的定义,律、令、各、式类似于正式法律的根源,礼类似于非正式法律的根源。 在唐代,律法是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礼是辅助审判的依据或解释论。 因此,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现代法的功能。 正如西方现代的“法”严厉指出的那样,“西文“法”字是中文的有理、礼、法、制四者的异译,学者对此进行审查。 ”。 (《严译名著丛刊门德斯鸠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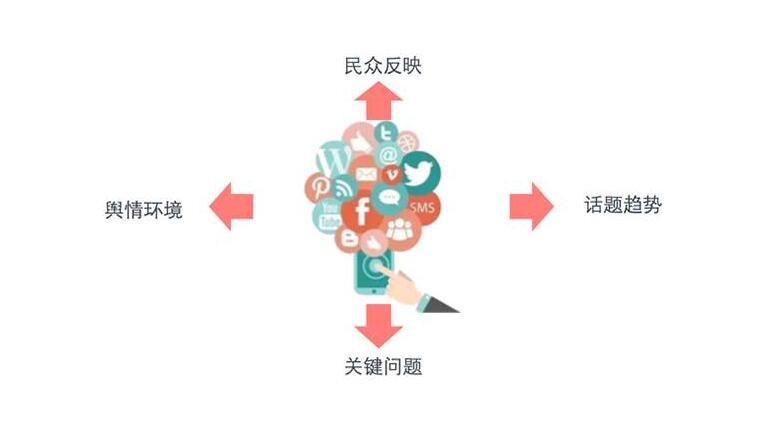
其中之一是根据律法定罪。 《唐律断狱律》明确规定:“诸断罪都必须有引用律、令、格、式正文,违反者必须攻击30次”,《龙筋凤髓判》的大部分案件严格按照《唐律》援引律文审判。 “少府鉴二条”第一条“鉴贺敬盗御茵席30事,大理断2500里”。 贺敬不服判决,认为偷的垫子已经分在御物中,但没有提交给宫廷,不能说是御物。 《唐律贼盗律》说:“诸盗御宝者,坐轿子服御物者,流于二千五百里。 」注:“是指供奉坐在轿子上的东西。 所谓“服被子、菌属、真、副等”,是指偷供奉给皇帝的东西,服包括被、褥子等在内的东西,和备件一样,采用了违反法律的行为。 张在判决书中也认为,贡品的各种,如果留给各部门,不用提交给宫廷,就可以推定为御物。 最后张主张“法有正条,理须正典”,支持根据原案的法律进行判决。

其二,根据礼裁判有道理。 《龙筋凤髓判》中根据礼审判是有道理的,但根据有无律文的规定分为两种情况。 1 .没有律文规定时,礼发挥审判依据的功能。 最典型的案例是违反礼制,就像“公主二条”的第一条。 永安公主结婚了,司发的礼金比长公主结婚时多20万美元,盖官邸的费用也一样,明显违反了贵贱长幼的顺序。 张先从礼义的立场出发,说:“小的不要大,一定会上下和平。 在说了“如果不是卑尊,那就是亲疏顺”之后,比较了这个事件,“先帝女的仪注,旧章程。 少公主的礼貌,但不能超越”,委婉地表示了公主结婚也不能超越的礼仪。 2 .有律文规定时,礼起道理论的作用。 唐代礼与法高度融合,《唐律疏议名例律序疏》指出“德礼是政教之本,处罚是为了政教,还需要意识阳秋相”,事件的说明论缺礼。 就像《左右羽林卫二条》的第一条一样。 羽林将军敬伟在皇宫警察着急时不怕危险,因“惩罚切门关、锺逆贼,清除宫禁”而获得嘉奖。 张敬伟认为“功不可嘉,议罪便当不敬”,“说到劳动不足,罪应该先结”。 《唐律卫禁律》规定“诸光圈进入宫门,徒两年”。 殿门,徒二年半。 打仗的各加二等。 进入内阁的人,互相扭打。 如果继续战斗,成为御所的人,就斩”。 敬伟没有诏令就擅自带着兵马入侵宫闱,触犯了律法。 张先生认为敬伟很有勇气,但擅自入侵宫廷不知道君臣的大体基本礼义,不能奏效,应该处罚。

二、人情是影响审判的因素
人情是“平凡的人心”,“龙筋凤髓判”中也出现了人情对案件审判的影响。 滋贺秀三认为中国古代法中的“情”大致有三个意思。 一是指故事、情况等事实关系。 二是“心”的意思,是活着的平凡人的心。 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 人情最接近“平凡人的心”的意思,“通常,人们可以估计对方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可以互相期待,互相理解”。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和民间合同》)“龙筋凤髓判”大多是关于职务犯罪的“公法”,根据这个定义整理“龙筋凤髓判”也容易找到人情的影子,第一表现三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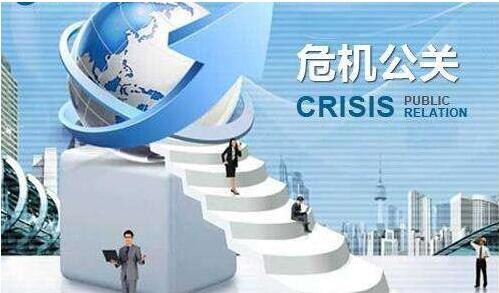
其一,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根据人情讲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张彝彟根据法律审判案,情说,情法并存,使判决更有说服力。 如《将作鉴二条》第二条所示,少匠柳奢负责三阳宫的建设,三个月就完成了建设,工匠因疲劳死亡的有十五六人,掌作官员为工作上楼选择。 《唐律非法兴律》规定“诸役实力,有不采用而采取的,计划不足,赃物论减少一等”,另外一步是“有做的和破坏的,别担心,想到误杀人的,只有一年半。 工匠、主司各以自由为罪。 ”疏议说。 “有修理运作和破坏·解体·拆迁等,首先不要慎重考虑,误杀人者只有一年半。 《工匠,主司各为罪恶》,还是工匠指的? 或者主司处分,各为罪过,没有连座之法。 ”在这次事件中,柳侘是主管建设三阳宫的官员,在建造宫殿的过程中,由于想法不够充分,导致工匠疲劳死亡,明显违反了律条。 在判决书中,张认为“为了丈夫半死不活地奏效,获得报酬”,用工匠的生命改变了宫殿的建设,但功劳不值得称赞。 他指出“法有正条,理宜科结”,应对了柳奢侈律处罚。 张先依法讲道理,然后依法定罪,谋求情法并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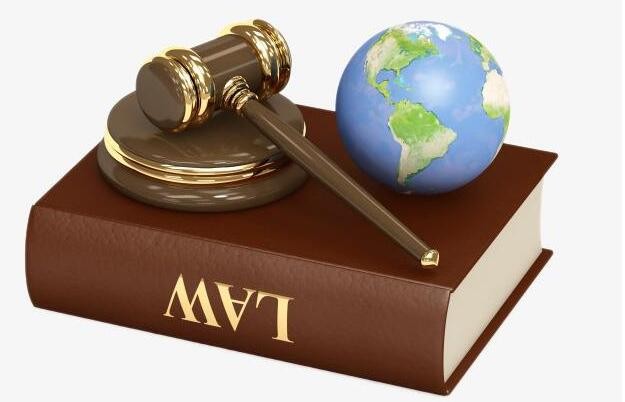
其二,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根据人情变通审判。 这种情况意味着相关人员违反了律文,但情本来就有,不管律文如何都可以根据人情改变审判。 就像《太史刻漏二条》的第一条,太史让杜淹私下教儿子天文,私下拿着“玄象器物”,违反律条,被指控。 《唐律职制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官方、私家不得有,违法者也两年”,注释为“私习天文者也一样”。 这个事件明显违反了律条的规定,但张认为杜淹不应该有罪,辩称“父亲是太史,孩子是天文”,“堂结构不跌,家风不落”,孩子接受父亲的作为,认为那种情况是应该原谅的,“准法是无辜的。 张不拘泥于律文,而是根据人情重新解释,作出无罪判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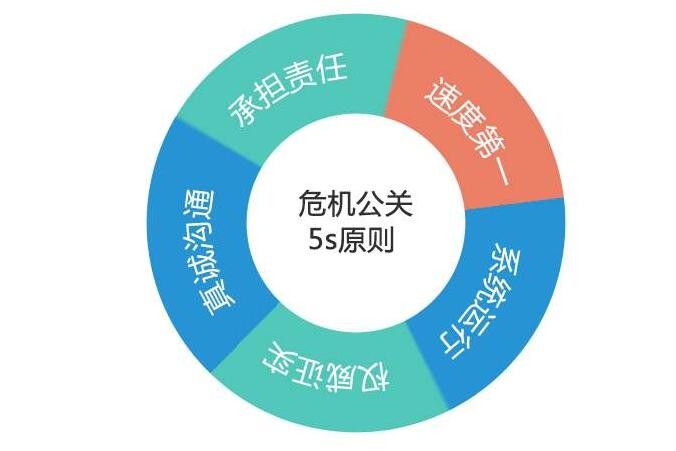
另外《太卜太医二条》第二条,太医令张仲景开了处方,私自加三味药,和古方出入,被绞死。 与配制制药中的过失犯罪“唐律”比较有确定规定。 《唐律名例律》规定“和御药合在一起,错误不及本方和封题的错误”。 另外,他还提醒说:“调配御药,错误与本方无关,写错了。” 疏议说:“和御药靠正方,但是是中间的错误。 《唐律职制律》中也规定,过失所致的合并御药“不如本方”的御医会被绞死。 疏散说明“不如本方”,是在两点多少不符合本方规定的情况下。 故意属于谋反。 但是,张在判决书中认为对张仲景的量刑太重,必须重新考虑律条和人情的关系后再进行审判。 他强烈赞扬张仲景的医术,表示事情是有原因的。 而且他承认根据律法对张仲景判处绞刑,但根据人情可以原谅。 “进弹劾扭伤,又甘于同甘共苦。 处方即依,诚苦闷”权衡后,认为皇帝能理解就有道理,认为皇帝不能理解就只能服从法律审判,应该衡量利弊后再作出判决,张显出了法与人情之间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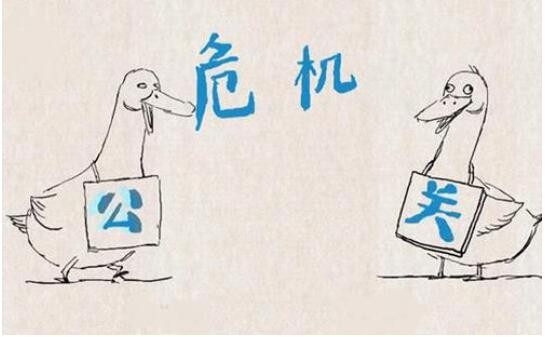
其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根据人情审判。 就像《苑总监二条》的第一条一样,新安谷水社本来就是皇苑官地,最近被民吞了,苑总监请求把民占领的地方重新放回苑内,民不服。 张氏认为新安谷水社是皇产的,但要权衡“利人”和“利国”的关系,不能因此伤害民众的感情。 “暂时不要伤害人民的感情。 最后张认为,本来应该不改变宫苑和庄稼地的界限,根据人情接受审判。

张有判决书中对律文的熟练运用和人情的慎重考虑,可以看出“不是违法的意思,不能违背人情”。 因此,“但是,因为知道堆栈故事,所以不能用遮光性的提案方法加深,很难阅读,一连串都很有意思”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也许是因为张彟判决书色彩风扬的复印件掩盖了他慎重缜密的思考,引起了后代的误读。 另外,《龙筋凤髓判》考虑到情法的优势对今天的案例编纂也有启示意义,一是应该鼓励非正式主体编纂案例集,有助于丰富案例研究的成果。 二是在编纂案例集时,选择例子不仅要考虑其法律价值,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力求兼顾法律和人情。
标题:热点:《龙筋凤髓判》中的法和人情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3/29612.html
上一篇:热点:临刑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