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明清治疫中徽州官民“义治”的作用
本篇文章5540字,读完约14分钟
明清时期,神州大地灾害疫情频繁,其中江淮一带、南北波及范围广,危害非常严重的大疫病有9次,惠州一府六邑幸免。 几年的大瘟疫,“强村巨室,知道的是莽”,民众对瘟疫的极度恐慌和无知进一步渲染社会恐慌,说“无知之民渐渐染上,直到骨肉不在乎看护者”,瘟疫的可怕传染性也是“父子不在乎”。

但是惠州一府六邑不像江淮其他地方“饥民掠夺四方”,兵燹不断发生社会动乱。 因为地方政府的社会限制措施和救助民众荒废义捐赠的“义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时期惠州疫情状况及优势
史载、明清时期惠州地区灾害次数达289多次。 其中,水、干旱灾害最频繁,疫病灾害共有14次。 干旱后,“人物交织而痛苦”(参见王志伊的《荒政编辑要》卷八《防止时疫》)。 灾后饥荒又说:“遮盖饥饿和寒冷的人民离家吃饭,日夜暴露。 或者暴露在风雨中一定会成为疫情的记忆”(《方苞集》下集外文卷五《徐蝶园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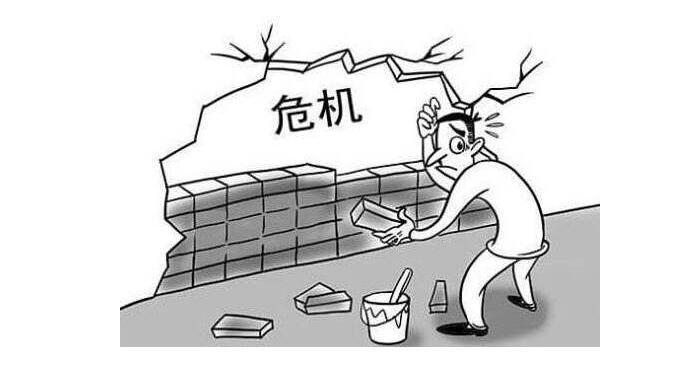
《惠州府通志续篇》记载惠州地区出现了“六邑饥饿,又大瘟疫”“大饥饿,斗米一分钱八分,民大瘟疫,僵直载道”,甚至出现了“孤村数无人烟”现象。 很多受灾者生病或流离失所,田地荒芜,粮食价格上涨。 《徽州府志》记载“戊子自己丑六邑饥饿,斗米一分钱八分”,据明制,一石十斗,即米一石需要银一二八分,万年平均米价在石六分左右,增加了164%。

万历十八年,面对凶恶饥荒不断、疫情严重的情况,时任职员外郎的邹元标疏远了万历皇帝。 “现在的人都知道救饥荒,不知道救瘟疫。 ”在户部间谍书中,他说:“之后,各省直遭遇重大灾害,向各府县承诺制作速申文,配合抚押,廉价移动分公司仓积谷和总部事例义负等银行。 病人喂食、买药饵解救、死者买棺材、义挥葬礼”(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2 )。 但是,这些基本的免疫对策必须得到皇帝的恩惠才能实施。 说明后期,朝廷在宋元时代设立的大瘟疫救济惠民药店等功能作用逐渐减弱,万历10年至18年发生全国瘟疫时,朝廷实际上没有系统比较有效的救济治疗方法。 朝廷腐败官僚怠慢,瘟疫蔓延加剧,社会动乱和盗情四起。

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安抚民心,惠州一府六邑一方发布了告发令,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嗯县奉行鹏好古宣布教师严厉打击盗贼。 “直到凶年,所有人都告诫说:宁死饥饿,无死盗”(万历《耶志》传卷一)。 另一方面,府县官员和各村民组织积极开展教师招揽,采取激励和控制措施,形式多样的民间救援对疫病的“义治”盛行,及时弥补了政府疫情救援中缺银粮食的空白。

“义治”在疫病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惠州地方政府和民居组织除了在灾害疫情中发挥非常有效的社会控制功能外,还鼓励和支持商人和乡贤乡高级化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灾害救援疫病义捐赠活动。

(一)惠州官民救济疫病中的“义治”措施
推进采用医药品打分丸。 疫情发生时,明时期全国各地普遍成立的小规模惠民药店不能满足社会的诉求。 江淮南北地方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经常积极采取措施,将救济治疗疫病纳入政府职责范围,邀请名医、制药分丸,鼓励民间“义治”。 在新安医学盛行的惠州,各地的新安医生进村给入户医生用药。 官府和民居组织鼓励和组织医生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活动,弥补了官府和民居组织救援疫病的不足,惠商们也积极解决了,形成了当地广泛称赞的“义治”现象。 明代医生张明征说:“世精岐阜,授课太医院官,之后归籍开馆药”,惠州村乡的“四方脚后跟来了,反应不累”(民国《婺源县志》的“人物义行”)。 嘉靖年间,“祁门县内疫情流行,死亡相继发生,哭声高涨”,祁门县朴树乡名医汪机“免费治疗,救人无胜算”。 汪机据报道“要求长期造福人们,应益博,活人达数万人”(李增水著《石山居士汪机传》)。 婺源县商贾程大防说:“病不能请医生,为了施处方药,很多地方都活着……邑侯重之,礼是宾筵。” 清代盐商汪应庚疫情“扬则施棺材、棉袄、设药店、济回禄、郑溺舟、弃婴”“时疫记忆持续,准备药饵,不计算治疗生活”(《王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

宣传备荒仓库,激励义仓建设。 一个是普建备用仓库。 预备仓是明代朱元璋首次推进的预备荒仓。 弘治《惠州府志衬衫政》称,惠州府的备用仓库数量足够,县府的备用仓库数量多为4个,逐年增加,休宁县增加到15个。 仓库谷的数量足够,弘治前全府备用仓库谷的数量实际上达到了23万石多,平均每人拥有近一半的石头救援粮食,杜绝了因大瘟疫饿死盈野现象的发生。 到了明中期,预备仓颓废,管理混乱,储粮减少了。 《惠州府志》中写道:“粜和赈济,大半充满胥市的狡猾之处。 乡民去领,忍饥受奶,在不索取往返费之前,中间带空囊回去”(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币六》)。 二是建设廉惠仓。 《惠州府杂志衬衫政》中记载:“正德十二年丁丑,知府张芹买了田三千亩,使六邑缺乏廉惠仓准备。” 受张芹太守之力,惠州六邑普建廉惠仓。 《婺源县志》卷十一《食币六》也记载了婺源县廉惠仓计“田二百六十六亩八分三厘一毫,年收入稻三百七十九石二升,张公捐赠赎所,储藏室准备救济”。 绩溪县廉惠仓《正德十二年知府张芹买寺田收集储藏不足,嘉靖四十年人宏济仓,万历四年,奉行陈嘉策重建》(嘉庆《绩溪县志》卷三《食品储藏》)。 可以看出,这种官僚性质的准备不足仓库在疫情时政府不能发放平买资金的情况下起着确保救援粮食供求的作用。 而且,政府岁银不足的时候,惠州有点富嘉乡的高级化会积极输给粟政府,确保粮食仓库的充实。 在《沙溪集略》的“祥异”卷中,记载了“干隆十六年辛未夏秋冬三点,干旱,红地千里,民饥饿食少,斗米五钱,知府何公达善,奉行王公鸣劝告捐赠减粜,里中批次捐赠米石救济民。 。 。 到了说明书的后期,廉惠仓逃不过被入侵的捕鱼不幸。 《绩溪县志》记载:“廉惠、仁济二仓收获的寺产银多被捕鱼侵害,民不经济”。 为了弥补政府救灾粮食储备的差距,惠州各村民组织积极介入准备不足,组织地方绅士组织义仓和社仓筹资演出。

三是义仓和社仓兴起。 义仓和社仓是民间资本的油谷备荒的仓库。 惠州早期的救援活动首先是乡坤和商人捐赠祠堂田的籽粮,帮助穷人。 明万年间,广德来自商耶县沙溪凌景芳,“特别是喜施和周急救济贫困”“捐资买田和家族饥饿和饥饿者,共计有几亩计划。 创业者和家族无根据者,共乐计都有几个。 又放下冢一区,没有家人死亡和归来的人。 家人养护致死并不遗憾。 》(干隆《沙溪集略》卷)嗯县令林元立对此很佩服,亲自制作了《凌氏义田记》《凌景芳者,其义士! ”。

明中叶后,为了弥补救援活动的空缺,惠州乡下的普建社仓。 根据万历《休宁县志》,万历9年,休宁县全境共有社仓37处。 祁门县奉行刘一爌在祁门县建社仓60处。 婺源县也有《四乡或义田为仓》(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币六》)。 社仓成立之初,储粮由官员提倡募捐,但首先是民间集资。 祁门县社仓官说:“本银四百七十一两买稻五百七十石,各送稻约,使乡约分各仓准备不足。”(道光《祁门县志》卷十四《衬衫政》)。 社仓义谷的发散和管理也由民间义士承担,政府只是起组织的指导作用。

用广泛的募捐救济饥饿的人们。 明早开始万年来的惠州府县积极准备足够的救援粮食金救济饥饿的人们。 从万历十六年到十七年,大瘟疫时,祁门县救济稻谷3151石、银1420两,受灾者达到12050人,杜绝了“道歹55相望”“人相食”现象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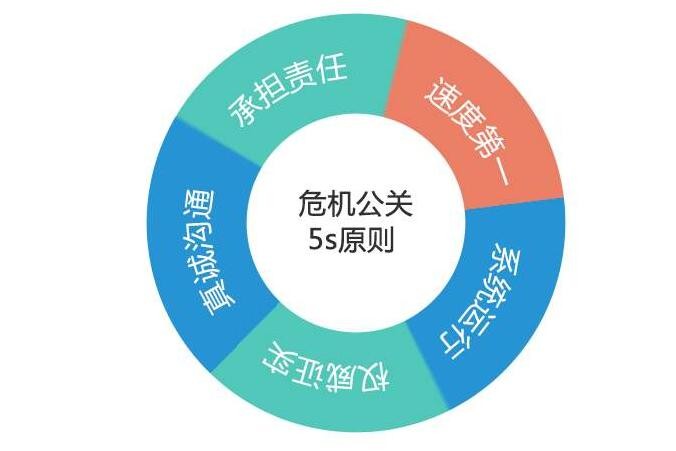
随着民居组织的推进,各邑贤达商人广泛开展了煮饭粥、煮饭银等救济饥饿人们的活动。 歙邑灵山的人们说:“佐彭侯(即彭好古)掉粟救济,但在背后计入口授粮食,生存非常多。”(道光《诶县志》卷八《人物志义行》)。 婺源县汪兆阳,《平粜施粥济饥饿,赖活无计》(干隆《婺源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义行一》)。 民国的《婺源县志人物义行》卷中记载了明代311人的捐赠粮食《义行》的惠州贤达逸事,当地政府积极提倡和鼓励乡民的飞跃捐款。 明狡猾县令在其《旌义堂记》中称赞了乡民胡彦本寄谷救济善行。 “正统辛酉年,赐给宰狡猾县。 岁旱饥饿,耆那民胡彦本慷慨解囊一千四百三十户。 受奏闻,以遣使谕谕、劳使羊酒、旌为义民,免于丁役”(嘉靖《狡猾县志》卷十四《艺文》)。 正统九年至嘉靖年间,狡猾县当地在捐献银捐赠谷善行义举中,根据朝廷和各政府敕令建立牌坊允,达到了7名代表功德的“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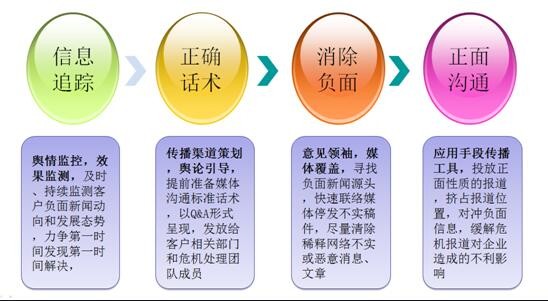
施棺材盖冢,盖肠埋胤。 大瘟疫之年,瘟疫死人的“多是记忆气体熏蒸造成的,一旦被掩埋,不仅会免除死者,还会免除生者和灾害条件的驱邪”(王志伊《荒政编辑要》卷八《预防·便雅悯时疫病》)。 所以,被礼貌地教导的惠州非常重视已故宗亲的安置。 除了政府机关设立义冢外,民间商人贾乡的高级化还致力于施棺盖冢。 没有棺材者给予”(弘治《惠州府志》卷五《衬衫政》)。 婺源县城西人汪逢阳,“性慷慨,勇敢行义”,万历十六、十七年,疫情发生时,施棺埋葬三百余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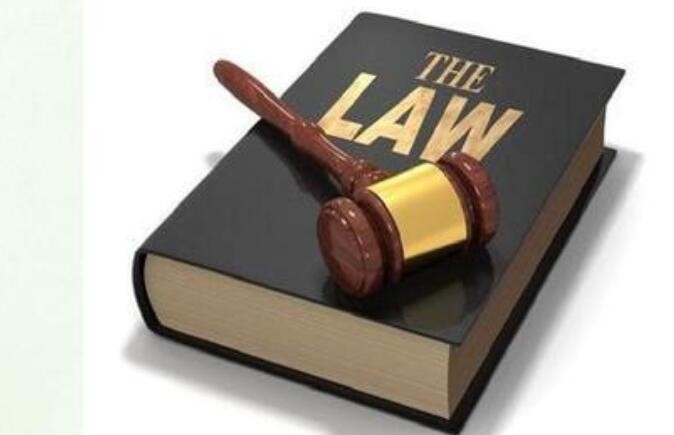
成化年间,歙县环溪商贾朱克绍在歙县二十七都汪村的捐赠购买地设立了义冢,“再购买地二亩准备每年清明日设置菜节”。 “成化十八年新安卫千户明明捐出自己的财富买山地的十余亩,穷人不能埋葬的话,就埋葬在棺材里。 上司入籍。 》明代诶县乡贤吴文光在万历饥荒大瘟疫时说:“糜烂粥为了饲养饥饿者,出钱出米周穷,所以施舍棺材埋头于辅助道”(民国《诶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

不仅如此,惠州乡贤广泛建设义宅,在灾害疫情中流浪,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避难所。 明治甲寅年间,诶县岩寺余姓乡民建义宅“为家几乐”是专门为在什么样的灾害疫情年摇晃漂流的受灾者和家人安身立命的,“所有家族的疏远和村民,听说住在一起”。 明徽州萧名大学士程敏政为此专门写了《佘氏义宅记》的评价。 “说到范之义庄,郑之义门,世界能看到很多吗? 情况来自一厢情愿,布衣之士可居其族,避之不及义和平! ”。

通商平粜,救灾民。 瘟疫年,政府和民间采取通商平粜措施进行救援,其中平粜粮食价格拯救饥饿的人们成为惠州民间参与“义治”救济的优势之一。 《沙溪集略》卷四记载了徽商凌顺雷灾害疫情之年冒着炎热奔波苏皖,购买谷米的“平价销售”轶事:“岁辛未旱饥饿,道殷相望,公虑市米不多,人有钱整日冒着炎热在江苏省之间买。 民国的《婺源县志人物义行》中也记载了程一庆的商人在“岁饥饿”时“降价平粜,远达数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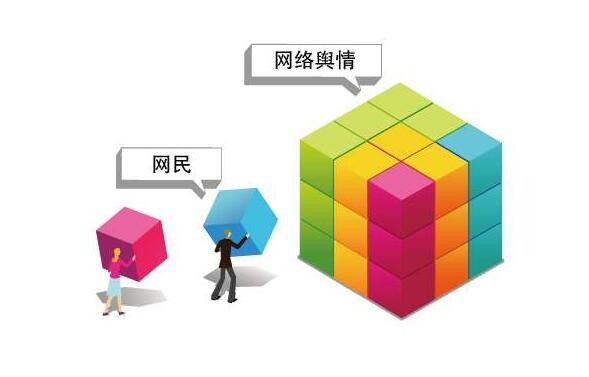
(二)“义治”在惠州官民救济治疗疫病中的优势
综合观察了惠州官民在明清治疫中的“义治”现象,表现出以下优势。
其中之一是参加者多,抢救疫病的阶层广。 疫情中不仅有惠州府县申报受灾银谷物救济灾民、减少赋缓、劝地方民间组织和乡贤商人采取救疫行动,还有各民族、乡贤商人和民众在兴起的银捐赠谷上粥粟等义捐救疫活动。 而且,政府鼓励富民平粜发出粟,给予年表,有力者不能给予惩罚。 各邑乡贤绅商协助官员和人民积极努力救援,普通老百姓也倾囊解救时疫。 歙邑谢氏兄弟,家只有女儿,但倾斜袋子给饥民。 惠州商人为了救瘟疫“不惜送上千金”(康熙《惠州府志》卷2《风俗》,卷15《尚义》)。 惠州上下合作,抵抗万人瘟疫,万历十六年、十七年瘟疫流行时,惠州瘟疫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无数人得以生存。

其二,很多人实行政策,正确拯救瘟疫。 惠州旱涝灾害频发的环境,使当地政府和民众积累了丰富的防灾疫病对策经验。 嘉靖时佥事林希元总结救荒有六急“贫民急粥、疾病贫民急医药、发病贫民急汤米、已死贫民急募瘗、儿童急收养遗弃、轻重为囚犯急宽衬衫”(王志伊《荒政编辑要》卷头“纲目荒政丛言”)。 惠州基本上在干旱后有大瘟疫,因此饥饿受害者的免疫力低,容易得瘟疫。 因此,在惠州各界的祛病自助中,以粥供给粟为主要措施,除了官员供给粟外,还组织家乡村民们广泛粥供给粟,消除疫眉。 诶县岩镇的吴文光先生说,“设置糜烂粥饲养空腹者,出钱出米周穷”的现象不胜枚举。 疫情发生时,义诊药成为控制疫情的必要手段。 惠州新安医学明代已经一体化,出现了大量的医学世家,当疫情发生时,新安医家将人们在危难中拯救。 休宁人馀淳精通医术,说:“万历戊子岁的瘟疫值得。 秘方都活着赢不了”(《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医部医术名流列传》)。

其三,惠州民间组织的领导率都成了治疗疫情的力量支持。 一是人们的组织化是领先的作用。 惠州人特别重视道德礼仪主义,惠州的“朱子至后,多明义理之学”,惠州社会普遍有书籍道理、循规蹈矩、修德崇善的文化传承,以此在灾害疫情时拯救穷人,拯救穷人,拯救穷人,以德之 二是尊重行善的捐款活动。 除了建立完整的社仓义仓捐赠管理制度外,广大组织族还积极参与粥捐赠粟的应用来拯救饥饿的人们。 鼓励和支持培养新的医药世家,聘请名医义诊,用药援助受灾者,组织义冢收集盖“陀道殣”。

其四,儒家义利观和仁爱思想的道德教化成为灾害疫病“义治”思想文化的根源。 在理学达人、惠州人朱熹的仁爱思想和义利观的熏陶下,“儒风独茂”的惠州社会形成了帮助贫困经济的习惯。 在惠州的人们看来,在大灾害的大瘟疫中,灾害救援施善,救助受灾者是无论是官方贤达还是平民都值得称赞的德行善举,表现为“族党的愿望”“祖先之光”“其关系非常小”。 所以,在这样行善的义举文化习俗中,惠州商人贾乡贤儒士热衷于义援救济,穷人也节食,依然是公走义“黾勉积累了十几年,暂且倾檀”(康熙《惠州府志》卷十五“尚义”)。 清干隆年间,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两淮盐法道员鲍启运两兄弟“置身体源户田五百四十亩,专门为家族之间给予四穷(男寡妇、寡妇、孤、独)而设,归诸宗庙”,鲍启运在瘟疫中成为“穷人、穷人” 由此可见,惠州官民“义治”在明清治疫中的善举有其道德思想的基础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承,对现在的抗疫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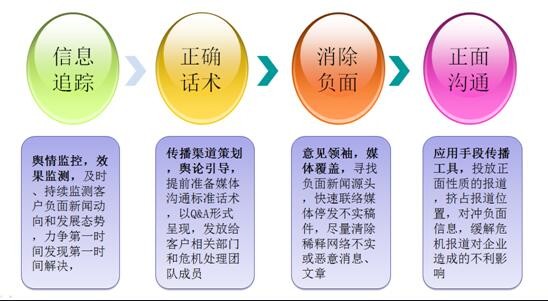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标题:热点:明清治疫中徽州官民“义治”的作用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2/29479.html
上一篇:热点:法律的眼睛
下一篇:热点:白居易与《甲乙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