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学术出版走出去 还需爬坡过坎
本篇文章3485字,读完约9分钟
原标题:学术出版要出去,爬坡。
前几天,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和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以“现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达”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学术界的30位专家学者分别发表了意见,面临着现在国内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困境。

一位学者坦率地说为中文学术著作找到好的翻译需要运气。 有些学者说自己的心血作品找不到好的翻译反而找不到。 目前,国内出版社多把招标方法作为学术著作寻找译者,但承担这一“摆渡人”的作用,很多时候对原著不太了解,有些出版社急于骑马,翻译成为流水线作业,翻译水平下降,

什么书值得翻译? 什么样的译者是好的译者? 现代中国学术如何真正“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比较有效的传达?
1、选择标准书- -译文,为了更好地对话
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和陈建华教授的《革命与形式——茅盾初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 1927—1930 )》(以下简称《革命与形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成为世界顶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荷兰博和学术 之后几年,经过译者多年的辛苦,两本书的英语版相继出版,在海外公开发行。

“好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社的灵魂和生命。 》研讨会上,荷兰博和学术出版社副总裁、全球销售总监focko van berckelaer就“如何提高国际出版成功率”作了发言。 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会报评价的《年度优秀学术出版物》称号,是学术出版社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中国的学术思想面向世界,参与世界学术交流,能说好中国的故事,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值得翻译的书是什么? 那些书适合“出去”吗?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认为其中一直存在认知偏差。 如何选择确实是个难题。 “很多收藏在海外图书馆的关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书不是高水平的学术书,而是嚼味道和蜡,很多好的学术书无法翻译介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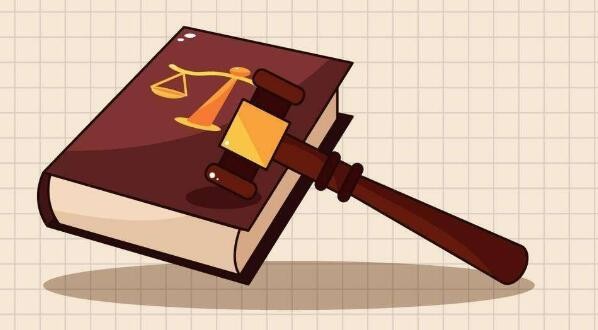
古典性、思想性、对话性——复旦大学华语系主任陈引驰提出了三点标准。 前两点不言而喻,具有强烈领导能力和思想史意义的学术著作应该重视其译本。 关于对话性,陈引驰说:“学术著作不是《德语》,而是有对话性的,翻译后是更广泛的对话,也是学术评价的一种形态。 会话不仅是中文的语境,即使是不同的学术文化以前传来的中,也有会话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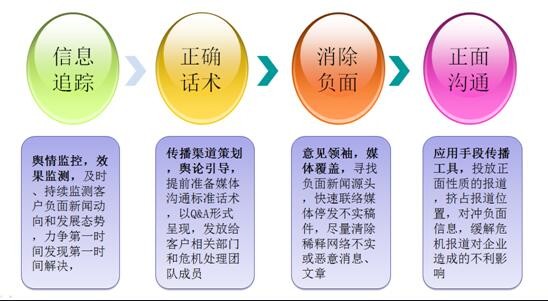
“现在翻译成外语的书不少,但真正的好书很少”葛兆光说,值得翻译的书不一定是非常精致的学术著作,需要看看中国以外的人需要什么样的书。 他认为三种书应该翻译成外语。 一是有中国特色、风格和问题意识的书。 一个是教科书和普及读物之类的作品,适合更广泛的读者。 另一本是年轻学者的书。 “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做得很好。 他们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但没有良好的学术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跃进教授说,在中国学术出版的“走出去”过程中,明显的问题是“错位感”。 我们想推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海外学者,但特别需要海外学者,我们推不出来。 他的观点是,选择准书一定要有“话题”意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网民都要找到有趣的话题,找到中外网民的匹配点。

“以前只考虑‘发售’,现在也在考虑接受对方。 除了找到共同的话题,还可以考虑找到同样的思想方法、学术方法。 ”刘跃进说。
2、寻找对方——翻译困难的再创造
葛兆光很重视译者的作用。 “全部翻译成外语的著作,其实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次创造的过程。 ”。
复旦大学史地理研究中心的葛剑雄教授承认,如果中国的学术成果翻译不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当时也有网友从沈从文访问美国刮起旋风,从东海岸飞往西海岸。 其实沈从文的很多回答都是胡汉斯翻译的,听众听起来喝醉了。 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确实,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副本要用另一种语言完美地表达,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和严格的。 思想和精神的翻译,学术观点的传达,特别困难,必须更正确正确地表达本意。

2005年,博和学术出版社发表了《现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策划了《博和中国人文件丛》和《思想、历史与近代中国》两大书系,翻译出版了中国学者重要的学术著作。 2008年在《中国思想史》英语版的出版上签了字。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出版质量,同行评审、质量监督结合了翻译过程。 在此期间,葛兆光与两位译者反复进行信息表达,也有反复进行40回合以上的讨论的章节。 《中国思想史》的复印件有1300页,为了应对英语网民,进行了大量的删除,最终删除到了660页。 经过8年的磨练,结果也令人满意——《中国思想史》不仅陈列了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的图书馆,还在美国choice杂志上被评为年度最佳学术图书奖,获得了海外的好评。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两位译者。 他们在八年里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认为在英语版中作者是次要的,译者是第一的。 ”葛兆光说。 《中国思想史》的默认网民不是入门者,而是有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写这篇文章时引用复杂的史料,有很多复杂的论述,认为很难转码成英语版。

葛兆光很坦率,在其著作翻译中遇到过一点不如意的事情。 《中国思想史》的翻译,2000年有人找过,译者在翻译另一本著作时百度复制放入一些东西,不要哭。 “找到合适的译者是最重要的”。

《革命和形式》的作者陈建华教授也承认,寻找译者是“需要运气的”。 “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很多从法语和德语翻译的学术著作,中文确实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和转换。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在文化语境之间存在一些障碍,需要贯通。 ”。 陈建华说。

关于跨境学术翻译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语版的主编吴冠军说:“我对社会科学类的翻译不太焦虑,文史哲的翻译可以说是《苦言》。 根据网友的不同,翻译后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新作品。 这不是语言的切换,而是两种不同语言形式之间的深度冲突。 所以,永远没有最好的翻译。 在这样不可能的情况下,只能制造可能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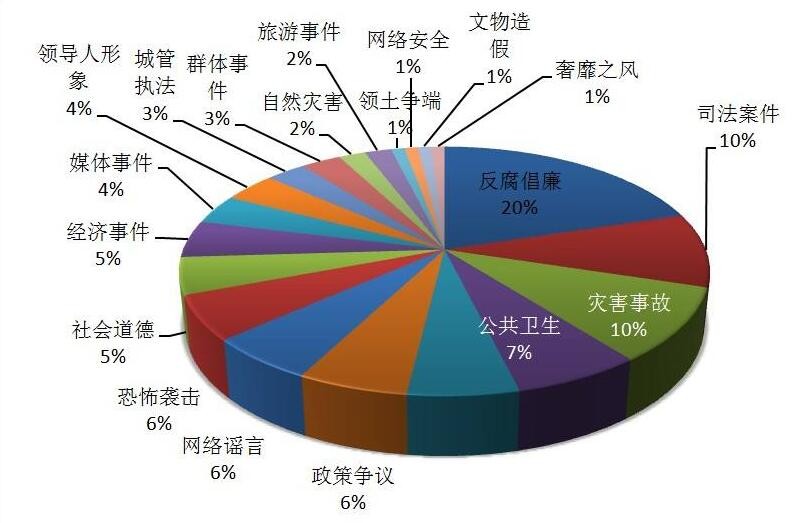
吴冠军说:“许多优秀的中国学者有非常深的学术积累,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这种偏见必须改变。 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西方思想呈现出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但中国思想重要的是带走学术的“负熵”。 ”。 如果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中国学术真的可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3、走远——做完才有生命力
我记得复旦大学史系教授章清拒绝了国内出版社的翻译申请项目。 “当时,我知道他们用招标的方法选择了译者。 除非做作业,否则很难保证译者的学术素养、著作的理解度。 他选择了“宁肯出不来”,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专业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潮流计划出版和之后的落地,翻译的复印和效果就与期待相差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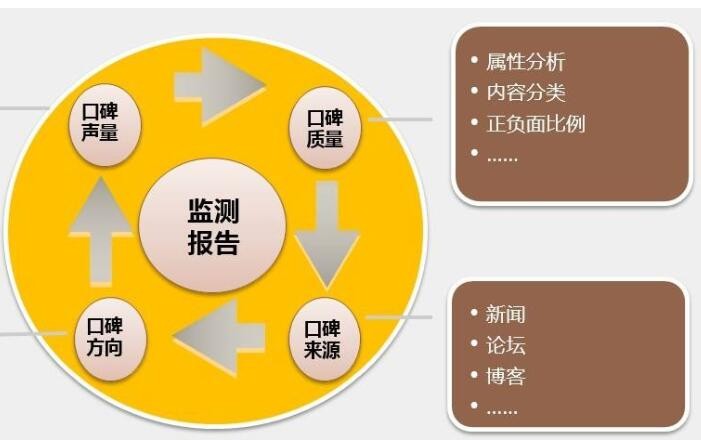
陈引驰谈了自己两次不愉快的翻译审查经验。 另一方面,选书中也有“销售型”的学术,引用丰富,但其本身没有内在的质量,缺乏会话性和原创性,不需要翻译这样的书。 另一方面,翻译的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只需注释的翻译是否“正确”就可以看出。 因此,有必要非常慎重地选择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合格的译者。

葛剑雄还说,应该把“扩大中国故事影响很大”的需求和“展示学术水平”的需求分开。 “不是说学术水平高、发行量大,而是必须有区别、冷静的头脑。 这样,就可以把经费花在地方,把作者和译者的精力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最适合翻译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认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对于不同的诉求,必须做不同的翻译工作。 ”。

复旦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严峰认为,高水平原创性学术著作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前提,国家支持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有力保障,高质量翻译是人文学术著作“走出去”成功的关键。 “我们必须出去。 不是我们想做什么,而是要考虑海外网民的实际诉求。 他们想知道中国的什么? 我们当然不是选择书的翻译,而是要向他们传达信息。 接下来委托什么样的人翻译也是重要的问题。 我的体验是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人能翻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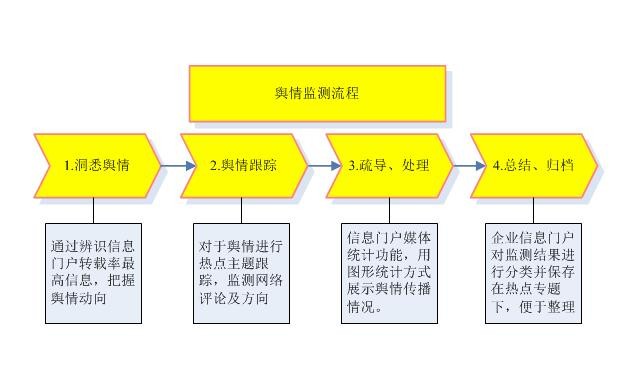
学术出版的“走出去”,真的要走很远,需要以网民方便而乐于接受的方式,考虑大众的普及水平。 刘跃进警告观察中西交流中的语言问题。 “过去我们的学术著作只谈学术,只在学术圈工作。 很多学者著作的味道嚼蜡,只是给自己看,别人根本不看,最多是自己的学生看。 学术到此为止,恐怕生命力也不长吧。 用人们喜欢的文案来表现困难的文案并不容易。 学者做得很深,“深入浅出”不容易,做和写就知道了。 ”。

专家坦率地说,“完成”通过接近目标用户,真的可以提高“国际可视性”。 出版界和学术界明确了目标网民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性,甚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可以更远、更准确地传达中国的声音。 (颜维琦)
标题:热点:学术出版走出去 还需爬坡过坎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305/38639.html
下一篇:热点:让版权闪耀恒久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