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明代商人文学形象的嬗变
本篇文章2229字,读完约6分钟
清明上河图的商店和商人
中华文明长期以来把农耕作为第一生产方法,从而历史上形成了“重本抑末”“重农制商”的观念。 即使到了清朝编纂《大清会典》,编者也感叹“崇本抑制末,载诸会典,著常经,由来已久”。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划分,“士农工商”的4人中,近代以前“商”一直处于末流。 尽管司马迁《史记》特辑《货植列传》中对该人的描述,但也有像弦高那样“有效追求郑国整体”、“谦虚无名、品行值得称赞的商人,但总体上对这个群体的负面评价不少。 《诗经卫风》中的乌合“二三其德”是背信弃义的小商人。 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句话叫“商人重利轻别”。 李益《江南曲》中感叹“与瞽塘贾结婚,朝错妾期”。 元稻“推定客乐”说推定客“虽然可以避免追求名字,但追求利益的是所有的营地”。 也看到了商人被淡义追逐的一面:“不要束缚同伴,卖假货卖诚。” 明代区起元用“客座奢侈语”为商人直接贴上了“小人”的标签。 “小人率商人多,君子资官禄。 ”从中国以前传来的学者的认识中,可以看出商人已经被认为是“重利轻义”的化身。

但是,观念上的谴责无法改变宋元以后,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将大幅增加这一事实。 即使在位于西南偏远地区的四川西昌地区,万年来有名的地理学家王士性笔下也是一派兴兴盛景,“苏杭新织织各种文绮,吴中贵介没有披,但他先得到了”,“犯了山海错误,咸的先尝到了”。 学者崇尚商人儒教也成为普遍现象。 袁宏道说,万历时期的徽商“竞相学习成为诗歌”,即使是不会写诗的人,收藏书和古玩的风雅也很多。 商人在经济行业的影响日益扩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

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启蒙思潮的兴起被宋明理学紧紧笼罩的社会所撕裂。 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袁宏道的“性灵说”,一定会肯定物欲,提高“重情”的旗帜。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打开了了解现代商人多方面的窗户。 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世界中,作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出现了与“重利”不同的“重情”“重义”的一面。 冯梦龙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有商人的生活和生意活动,凌晨初的《二拍》(《初刻摄影惊喜》《二刻摄影惊喜》)的近二分之一的编辑目的。 尽管这些作品的商人依然过着“百尺竿头五两斜,一生无处不在”的生活,但其中也有狡猾的不仁商人,但也有很多符合儒教以前流传的“士”品格的商人。

包括艺术的再生和想象的成分,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晚明市民文学所表现的城市生活形象依然现实,商人生活的描写就是其中之一。 像“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样的卖油郎秦重,是农民质朴善良性格的小商人。 秦重对社会底层出身的女性辛瑶琴有朴素纯洁的感情,与上流阶级孩子吴八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辛瑶琴说:“忠厚正直,又正直,又知道,知道兴趣。” 秦重兼具士、商的双重特征,他以真相荆瑶琴本改变了世家儿子登顶的心态,感叹“布衣素食,死而无怨”,秦重也可以说是“重情”。 《吕大朗是金完骨肉》的布商吕玉在厕所里捡到二百两银。 “等到坑厕所的左边附近,等着有人来抓,就把原物还给他”,等了一整天。 之后,我在南宿州遇到了失主,带他去扬州,把钱还给了失主。 他的善行不仅帮助别人渡过难关,还为自己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骨肉。 “润泽滩阙遇友”的纺织丝绸贩子认为失主可能是“卖家”或“丧命”,当场等了半天,把钱还给了失主。 失主朱恩恩和滋润为重情义结缘,互相帮助的故事也有告诫的意义。

比起儒家以前传达的“仁”“义”等观念,“情”更反映了人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优势。 中晚明受启蒙思潮影响的文士对越来越盛行的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突破了“商人重利轻离”的观念,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商人“重情”“重义”的一面。 从“重利薄情”到“重情重义”,冲击了商人从前传来的认知,也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商业活动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士商之间新关系的形成,客观上为文学作品中的“重情”“重义”商人形象提供了叙述空间。

明代中后期的“士商互动”越来越紧密。 对住在城市的文员来说,他们长期混杂在市井众生之间,越来越多的机会与各种商人近距离接触,长期受到城市文化和市民意识的渗透,生活习惯、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兴趣开始发生变化。 以李梦阳为例,他的《空同集》中保存了很多汪昂、馀存修、王现等与商人交流的复印件。 在为鲍弼写的《梅山先生墓志铭》中,李梦阳与鲍弼谈笑,详细叙述了亲密的情况,在听说鲍弼去世后,“楹俳彷徨”这种深切的哀悼之情,可以看出友情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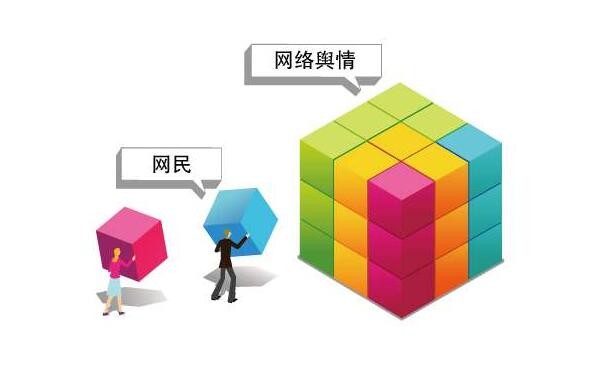
明代后半期的“士商合流”现象,使士商以前流传下来的边界逐渐模糊,学者商也不再是玷污个人清白的行为,很多文人墨客投入文化商业活动,参与文学创作,也参与了图书销售的经营。 商对士有很大的影响,士也逐渐改变了轻商思想。 这样的变化可以填补士、商之间本来就无法逾越的偏见差距,文士不仅高瞻远瞩地批评商人,还切入商人的日常生活,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知道他们的美丑善恶,商人的形象从简单开始 赞扬、肯定人性的美德,鞭策、否定人性的恶性,真实客观地在人类面前表现他们的形象,体现了时代的特色。

明代不能彻底打破“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以前传达了出租车贵商的廉价思想,从早期单一的“重利轻义”扁平人物中出现了表现“重情重义”的多种风格,使商人形象更加立体,丰富了文学史
标题:热点:明代商人文学形象的嬗变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2/29393.html
下一篇:热点:“业精于勤,荒于嬉”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