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勿忘先祖理想
本篇文章1836字,读完约5分钟
□沈小兰
第一次听说沈家本的名字是在“文革”后期,阿姨家。 那时,阿姨家在假山树屋,只有两家,简陋地被破坏,失修多年的凉亭被改建,杂乱无章。 在多雪的冬天,那所房子漏风或摇晃,好像随时都倒不下来。

春节前夕,我们从遥远的陕北高原回到北京,总是在阿姨家包饺子,不太容易重逢。 你还没有从“解放”的阿姨那里听到“你知道沈家本吗?
不知道我们兄妹三个,异口同声,茫然:他是谁?
总是快嘴的阿姨保持沉默,什么也没说。
沈家本这个名字,在我们心中扎根了。
10多年后,弟弟带我去金井巷1号---沈家本旧居时,这个祖先,我们还不知道很远。 原来三进的大院,破败纷纭,与任何北京的大杂院匹敌,挤满了居民。 紧挨着园门的二楼藏书楼,书香消失了,把狭窄的木楼梯逼得走投无路,油漆脱落了,踩在上面,吱吱作响,二楼过道里塞满了蜂窝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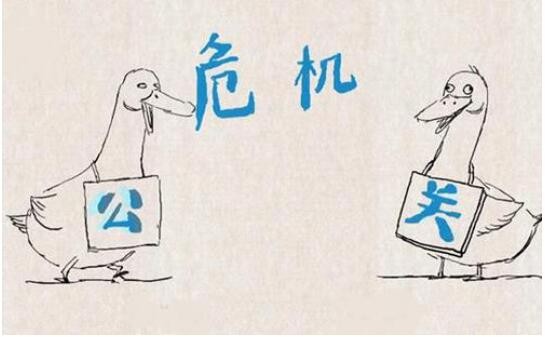
阿姨说她和我们父亲出生在这里。 我们曾祖父沈承熙是沈家本的长子,祖父沈仁垓就读于北京化石桥法政专科学校,为谋生在董康主持的法院担任书记官。

我和弟弟出生在南方。 我没见过祖父。 在哥哥的记忆中,祖父的形象也很淡薄,记得他很瘦,很少说话。 在阿姨眼里,祖父是个胆小胆小的人,一生小心翼翼。 虽然穷,但为了面子而死,那也只能负罪。 父亲从13岁开始卖文补充家庭。 用很少的稿费换了肉。 对不起,我拿到手了,用报纸包起来,塞在口袋里带回家了。 我无法想象。

阿姨给我发了她和父亲小时候的照片,上色了。 父亲文弱瘦弱,鼻梁上戴着眼镜。 阿姨还是三四岁的样子,弯着红嘴唇,弯着腰。 爸爸的阿姨八岁,同样有一双阴暗深邃的大眼睛。 父亲眼里弥漫着多疑的忧郁,少年老成? 阿姨不一样,黑色和深邃的大眼睛里落着火花,好像笑嘻嘻的。 阿姨说她不像沈家人,她就像带佣人一样,手一张张,嘴一张,工作麻利,说话也麻利,然后敢做。

但是年轻时的阿姨崇拜我父亲,捡起了父亲读过的书。 20世纪40年代初,父亲去晋察冀投身革命。 出发前,回到金井巷1号,在沈家的老家,和家人告别。 三叔沈厚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时,父亲回到老家和家人告别时的样子,感慨万千。 在他眼里,那时的父亲,虽然语言很少,但给人一种为拯救危难民族而献身的感觉。 人虽文弱,玉树临风。

父亲离开不久,阿姨也参加了北京地下党。 作为教师掩护,收集情报,把收音机藏在家里,向根据地传播情报。 而且,总是胆怯的祖父没有指责过阿姨,给了她很多帮助。 阿姨的老战友们说阿姨是年轻的女性,但遇事不慌不忙,大胆细心,一遍又一遍地把危险变成了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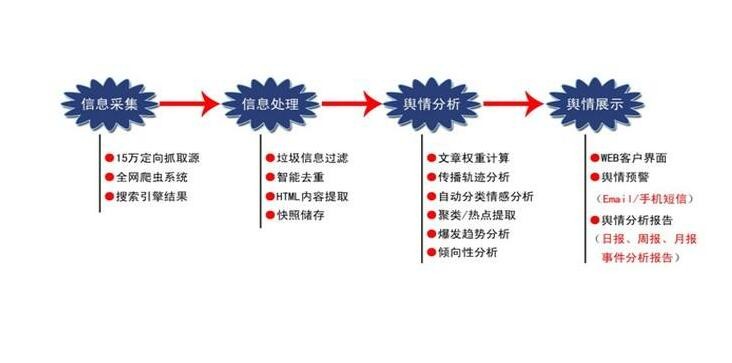
父亲和阿姨都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但是,我忘不了父亲的苍白和忧郁。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很苍白。 因为很瘦,他的白衬衫和灰色衬衫都像云一样,里面充满了风,飘来飘去。 他保持沉默,抽烟,下围棋。 在安静的深夜,一只手夹着烟,一只手拿着红笔,在灯光下细致地删改报纸的样品。

在比戏剧更疯狂的“文革”中,父亲的经验沉浸在泥沼中,被解职、挨打、没收家产、劳动改造,母亲好像又他离开了世界。 和父亲生活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晚上,我经常听他说话。 哥哥远在北京,弟弟小,只有我。 在那种情况下,父亲最需要的是说话,有人在听他说话。 一杯红葡萄酒,一根烟,不敢开灯。 烟头上的红光燃烧着窗外的黑暗。 他说他有读过的书和经验,弯弯曲曲。

后来,这点温暖也没有了。 病重的父亲也像母亲一样,离开了人世,忧心忡忡地离开了。 1969年的重阳节,父亲50岁。
性格决定命运? 阿姨的命运和父亲大不相同。 但是阿姨说她喜欢读书,早点出去工作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拓展了她。 在“文革”中阿姨也很得体,一个人关在高楼的一所房子里。 但是她不像我父亲那样忧郁,经常在深夜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空是明朗的一天,五月的花……因为唱歌她被骂过,在会议上被批评过。 但是,她终于爬起来,“四人组”倒下,再次回到了职场。

父亲的真名是沈厚淦,后来改名为沈育。 《文革》前是《安徽日报》副总编辑。
阿姨的真名是沈厚钤,后来改名为沈千。 我一直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 2007年去世,去世前是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我在安徽合肥的大蜀山陵园为父母们种了小松。 树下立着一块小石碑。 别忘了在石碑中间。 右边下面,我们兄弟三个名字中,冰雪兰一个词。
别忘了我们的父母因为没有法律保护而失去了生命。
别忘了祖先沈家本的改良理想。 用法律保护一般大众的生命财产和安危,为民族的繁荣用法律护卫。 (作者是沈家本先生五世的孙女)
标题:热点:勿忘先祖理想 地址:http://www.leixj.com/gy/2021/0122/29290.html
上一篇:热点:献给生命的颂歌
下一篇:热点:怎么真诚地面对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