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非法性”是明确融资活动罪与非罪的界限
本篇文章3498字,读完约9分钟
王新
◇为了严格掌握正当融资行为和公众存款非法吸收罪、集资诈骗罪的边界,正确掌握集资犯罪中的“非法性”,有必要研究“非法性”的认定标准、内涵、认定程序等层面的操作问题。

◇“非法性”的认定基准从早期开始就仅限于“未承认”。 司法解释将过去“非法性”的一元认定标准变更为二元标准,具体是形式认定标准,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非法性”评价的通行标准和具体化规定。 实质性的认定标准是以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在正当融资和非法集资之间,行为以每人平均筹资为平台和载体,但两者的法律性质完全相反,“非法性”是区分融资活动罪和非罪的边界,也是融资行为的刑事法律风险边界。 但是,对于“非法性”本质特征的认定问题,司法实践存在很大的灵活性和解释空间,为了严格掌握正当融资行为和公众存款罪的非法吸收、集资诈骗罪的边界,正确把握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非法性”

集中标准:“未批准”的形式标准
由于我国非法集资管制法规范的迅速发展变化,“非法性”的认定标准从初期就仅限于“未批准”。 例如,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79条中,对“非法性”的采用用语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鉴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了变化,2003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第81条评价为“未经国务院银行领域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审理欺诈案件具体应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律人、其他组织或个体,未经权利机构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由此可知,在关于非法集资的早期司法解释中,“非法性”被限定为“未经权利机构批准”形式的认定标准,对于批准的主体,使用了高度概括的用语。

二元标准:形式标准+实质标准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1月发行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问题的通知》(以下称为《取缔通知》)第1条规定:“(1)有关部门未依法批准。 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筹款和有批准权限的部门超过权限批准的筹款。 (二)约定在一定期间内偿还出资人。 除了以货币形式除以偿还利息的形式为主外,还包括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 (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的社会公众筹集资金(4)合法隐蔽非法集资的性质。 》在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发表的《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的几个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为《非法集资的解释》)中,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基本上是上述《取缔通知》中的非法资金 这个具体的表现是,将“取缔通知”中规定的“未依法批准”和“以合法形式隐藏非法集资的性质”这两个本来单独并列的优势,共同整合到“非法性”认定的选择要件中,具备其中之一。 对此,在沿袭《取缔通知》的行政规定的基础上,司法解释将过去“非法性”的一元认定标准变更为二元标准,具体如下。

(一)形式认定标准: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这是“非法性”评价的通行标准和具体化规定,不仅便于司法操作,而且符合我国吸收公共存款的审查制法律规定。 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应对新形势下打击新型非法集资活动的需要,确定未经批准只能适用于法律确定规定中未经批准的非法融资行为,包括合法借贷、民间资金等 被承认的一切都不合法,被违法承认,被骗取承认的筹款行为依然是违法的筹款。 对于法律已经规定了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没有必要考虑是否批准的问题。 对于以生产经营、商品销售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是否批准没有直接评价的意义。 因此,“非法性”包括但不限于未批准。 换言之,如果将“非法性”的认定限定为单一的形式认定标准,则无法满足打击非法集资的实际需要,成为产生二元认定标准的现实推动力。

(二)实质性认定标准:以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纳入“违法性”的认定范围。 如上所述,这个司法认定标准来源于“取缔通知”,但语言有所变更,从“隐藏非法集资的性质”变更为中性词“吸收资金”,放弃了否定评价的用语。 因为这个标准是实质性认证的范畴,所以不是批准与否,而是批准与否。

二元标准的新快速发展
在《非法集资处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2条中,非法集资被定义为“依法不允许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不特定对象或超过规定人数的特定对象集资,约定偿还或支付报酬的行为” 金融管理法、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细分后,“非法性”的认定标准再次迅速发展,被定义为(1)依法不允许的两种类型。 对此,基本保存了现行司法解释中的形式认定标准,其中的“承认”一词变更为“许可”。 在外延方面,“许可证”必须比“批准”更广泛。 例如,在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中,事前备案是指备案登记手续完成后开始活动,体现了承认制。 这相当于将依法未事先备案的筹款行为等纳入“非法性”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非法筹款的打击范围。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取消了现在司法解释中的“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的实质性认定标准,是一大进步,可以说是肯定的。 但是,应该知道,该认定标准实际上适用了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新闻的罪中,关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非法性”的用语,法律的外延依然广泛。 现在,也参考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将“非法性”一词的“法”范围限定在“违反国家规定”的水平,展示了行政主管部门防止特别保护金融部门利益的行政规则介入,防止非法经营罪被司法滥用的成功例子 例如,“审理非法集资的解释”第1条规定本类犯罪“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的规定”,从法律用语来看,这种解释采取绝对的观点,完全排除国家规定以外的部门规则,成为认定“非法性”的依据。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公布的保护民营公司快速发展的执法司法标准中,严格掌握非法集资“非法性”认定的,以商业银行法、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方法等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为依据,中国人民银行, 由此可见,这个司法标准采取了“可供参考”的部门规章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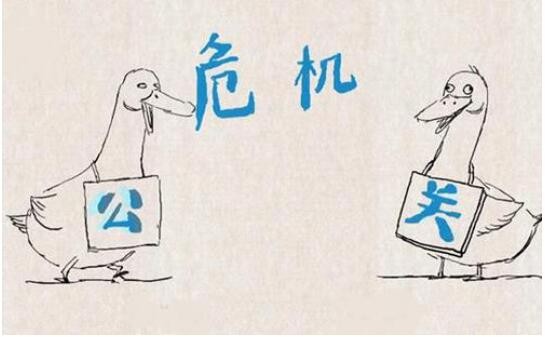
根据上述司法标准,“两高一部分”在年度联合发行《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第1条关于非法集资的“非法性”认定依据问题上,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时,要根据“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对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只有大致规定的,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制定的部门规章或者国家金融管理的规定、方法、实施细节 ”对此,该意见继续采取中间角度,但发展迅速,将“可供参考”的部门规则的前提限制在“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只做大致规定”的行业。

“非法性”认证的行政程序前置流程
关于非法集资案件性质的认定,国务院在2007年发布的《处置非法集资部时的联合会议机制》中,指出:“1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策界限明确的情况下,案件发行地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的体现。 性质认定后,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组织进行调查和后续处分。 2 .重大事件,跨越省(区、市)达到一定规模的事件,前期调查取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现行法律法规不明确而不定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后,按要求报告, 》这是行政程序中规定“非法性”的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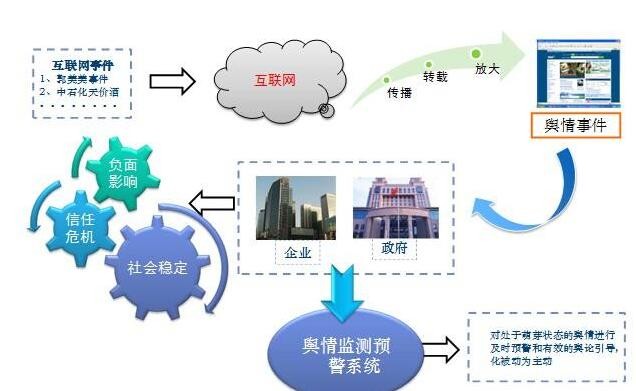
在打击非法集资的司法实践中,民间集资行为有时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和同意下进行的,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发表的《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中表示:“行政部门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是非法集资。 行政部门对非法集资没有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判。 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审理具体应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认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对于案件多而杂,性质认定困难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关于是否符合有关部门领域技术标准的行政认定意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性质认定。 ”由此可见,对于“非法性”认定的行政程序前置问题,该通知是为了保证及时打击非法集资行为而采取否定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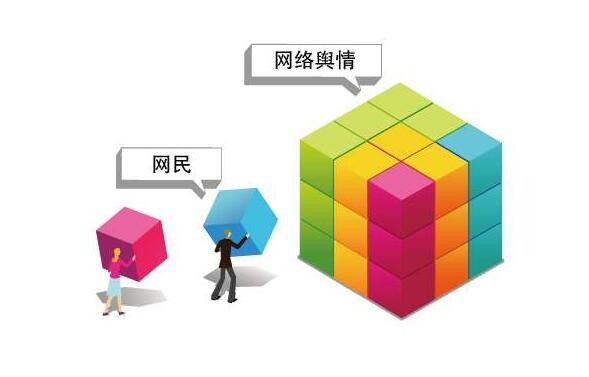
另外,年“二高一部分”《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基本上是“行政部门认定非法集资的性质,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手续。 行政部门对非法集资没有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必须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对于案件多而杂、性质难的案件,可以参考有关部门的认定意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性质的认定。 》非法集资属于行政犯的范畴,认为在司法认定时完全排除有关部门对“非法性”的认定意见是不现实的,是可行的,因此该意见中否定行政程序前置的角度较为宽松,可以“参考”行政认定意见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标题:普法:“非法性”是明确融资活动罪与非罪的界限 地址:http://www.leixj.com/pf/2020/1223/185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