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实事求是是刑法重要的品质
本篇文章2618字,读完约7分钟
事实上的要求是法律和司法的共同质量,包括民法、行政法,应该说要真实反映客观世界,体现客观规则,处理客观问题。 我们会产生客观真相和法律真相的差异和对立,但这是价值追求的目标问题,而不是质疑真实性本身的法律价值。 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真实性问题更重要。

一、刑法最基本的真实性是“无行为没有犯罪,无犯罪意图也没有犯人”
把个人的自我思考和心理活动认定为犯罪行为是对事实的一大扭曲。 近代刑法被启蒙以来,罪刑法适应罪恶被明确为刑法的铁律。 但是,主客观相统一是否大致属于刑法的基本还存在争议。 主客观相统一大体上随着罪刑法定对反对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有些学者质疑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模糊、摇摆不定。 但是,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任何犯罪都必须在罪刑法规定的框架下具备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和主观副本。 无论是形式的解释论还是实质性的解释论,都必须处理犯罪行为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复印件,不排斥特定行为就需要符合相应犯罪构成要件特征的主观复印件。 这不仅是犯罪刑法,也是对犯罪行为的客观真实的反映。

刑法中有规定法律拟制条款即转化犯的法律条。 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刑法将a行为视为b行为。 但是,由于a和b之间的行为和主观复制的不同,有时会引起很多理论争论。 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集体吵架,造成重伤、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有罪。 理论上对集体暴力造成的重伤、死亡情况是否包含主观过失有很大的争论。 一点学者认为,如果集体暴行使人重伤和死亡,行为者应该主观上有重伤或杀人的故意,不应该包括过失的行为。 但是,其他学者认为,如果暴徒因过失而重伤、死亡,则应该转变为故意伤害(重伤)罪或故意杀人罪。 否则,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将失去拟制规定的必要性。 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无论争论观点本身是否正确,现实中,集体暴行对他人的重伤或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行为者无法控制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瞬间的主观状态非常难以评价。 行为者的“疏忽”和“过度自信”经不起推敲。 这带来了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法律制定条款中存在的现实性。 如果没有客观世界的这种事实基础,把过失的行为变成故意的行为,在逻辑上和合理性上都明显是错误的。 客观上我们认为集体暴力造成重伤或死亡的行为者主观上可能有过失的情况下,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不被视为刑法的拟制条款,只是提示性条款。 总的来说,即使是刑法的拟制条款,也不是刑法本身的虚设,只是客观现实的僵硬和概括。

从司法现实来看,下行人的主观往往不容易用外观行为来评价。 理论和实践习性用推断故意的方法评价行为者的主观。 但是,推定是经验法则的妙招。 具有“双面刃”的属性。 对经验法则过于自信,忽视例外的话会出错。 虽然是经验上的推测,比如“天下乌鸦通常是黑色的”,但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其他颜色的乌鸦。 司法人员在采用推定时不要自信地一概而论,要小心。 在刑法条款或相关司法解释中,提示行为的主观副本或主观超额因素没有立法者或解释者的理由而不喜欢。 关于行为的规定即使一般和高概率地显示行为者的主观副本和主观超额要素的状态,也不能无视条文中的主观副本和主观超额要素的规范要求。 例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对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分别采用虚假说明文件和虚假保证文件。 但是,不能毫无例外地将在履行合同或贷款中采用虚假说明书的行为推定为欺诈的故意。 另外,关于非法集资行为者的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解释总结了携带集资逃跑、将集资用于赌博等,可以认定行为者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是,拿着集资逃跑,把集资用于赌博依然是经验上、涵盖性很高的评价方法,不能绝对化。 在某些情况下,行为者携带少数集资逃跑,或为赌博持有少数集资,客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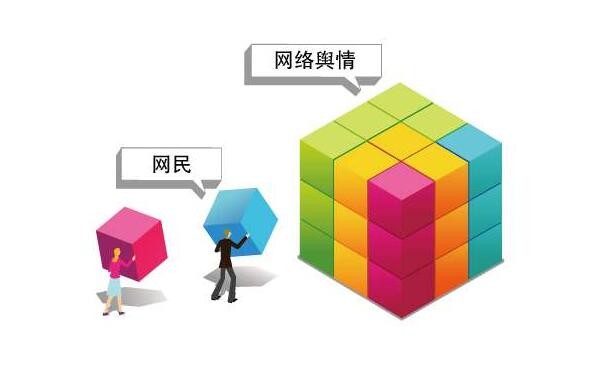
二、刑法本身受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指导
但是刑法有自己的法则,它有自己中立的理性。 这种中立理性的最大特征是刑法不应该人为地提高一种行为的属性。 刑法需要大力服务某一时期的刑事政策,它可以是“世轻世重”,也可以是“广严相济”。 但是,它不能脱离事物本身的属性。 刑法不能把过失的行为认定为故意的行为,不能把轻微的行为认定为重大的行为,也不能不分例外情况一刀切。 例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有些地方出现确诊或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不服从隔离治疗措施,出入疫情较多的地区,出现发热等感染症状,依然有意识地隐瞒进入公共场所。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必须以危险的做法以威胁公共安全的罪名被定罪。 但是,这些行为者的大部分虽说是“故意犯”,但绝对能肯定有威胁公共安全的意图吗? 事实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某些疑似患者和进出疫区的人故意隐瞒病情,进入公共场所,追求或放任威胁公共安全的结果。 完全肯定的逻辑评价可能没有延迟。 因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定罪时,可以比较客观地概括行为者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特征。 在“两高二部”的《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预防和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中,确定了行为人实施前述行为,主观上有传达新型冠状病毒的意图,可以用危险的做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很明显,具备传达新型冠状病毒的故意,拒绝隔离治疗,脱离隔离治疗进入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是以危险的做法认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统一的复印件。 司法解释推断故意陈述的隐含前提应该认识到总是主客观统一。 司法解释不能设立刑法的模拟条款,其经验归纳往往不能包罗事物的逻辑滞后。 对于上述情况尽快“一刀切”,误判的风险很高。

三、刑法实践还必须保持抑制的理性。
即使贯彻广泛严格的刑事政策,事实上也需要追求的政策态度。 严重危害社会、严重违反人们良知共识的犯罪行为受到严厉惩罚,迫于生活,对由年轻无知等实施轻微犯罪的人给予广泛惩罚,这本身就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真相的感情。 刑法事实上只是体现了人们的这种感觉和认识。 如果刑法没有客观地反映这种感情,就会失去法律的正义属性。 例如,严惩黑恶势力不仅是因为社会危害性,而且人们深恶痛绝。 但是,即使是执行重大政策的扫黑行为和突发疫情对策,将不属于黑坏分子,或者将威胁公共安全的犯罪纳入黑坏分子的范围,或者认定为威胁公共安全的犯罪,也不是彻底的刑事政策。 客观、克制和事实上的要求是刑法的自我理性。
标题:普法:实事求是是刑法重要的品质 地址:http://www.leixj.com/pf/2020/1221/17666.html
上一篇:普法:刑事审判中方言应用问题探究
下一篇:普法: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司法反思



















